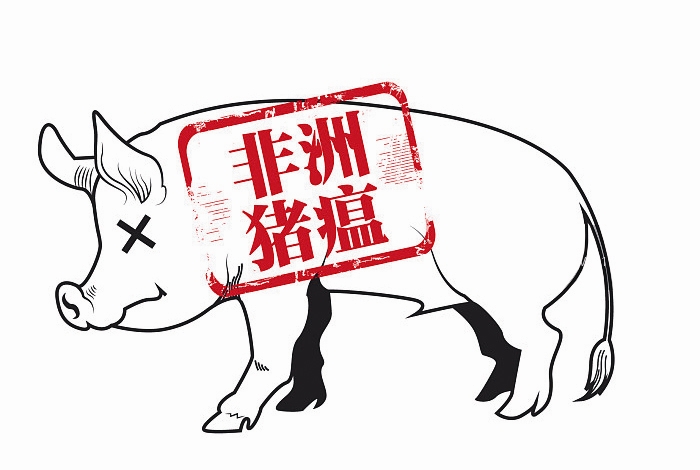《1936年的温州》珍贵资料影像曝光 谢福芸对温州有一种特殊的眷恋

谢福芸

苏慧廉全家福,右上为谢福芸
温州网讯 近日,随着《1936年的温州》珍贵资料影像曝光,谢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1885—1959)这个名字也被许多温州人记住。
谢福芸从小跟着父母生活在温州。她的父亲、英国著名赴华传教士、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苏慧廉说得一口正宗的温州话,并在温州办教会、办医院、做教育,所以谢福芸对温州有一种特殊的眷恋。
1935年5月,苏慧廉在牛津去世。谢福芸于1936年7月重返中国,并于12月到访温州。
温州是她度过美好童年及少女时代的地方,也是她全家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谢福芸抵达温州的那天,正是西方的圣诞节。1936年的圣诞节有点不寻常,因为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正是在这一天得以解决。作为英国外交官的遗孀、中英关系活动家,谢福芸在南方小城目睹了温州人如何度过这一天并看待这一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
在温期间,她还走访了白屋、白累德医院、城西教堂,并碰见许多旧雨新知。
谢福芸后来回英国,把这段见闻及思考写入《崭新中国》(Brave New China)一书,并专成一章(第二十七章),取名《圣诞佳节》(On a Christmas Day)。目前东方出版社已汉译出版谢福芸的四卷本中国见闻录。
谢福芸一生六度来华,走过大半个中国,认识了很多中国人,更见证了诸多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她的聪慧及学识,加上她父亲、夫君的人脉,为她深度了解中国提供了一般人不具备的条件与资源。谢福芸对中国既满怀深情,亦有旁观者的冷静,她“赞扬他们的美德,宽恕他们的瑕疵”。她的“小说”,比我们看的历史书更富细节,也更有人性。
2018年8月23日至25日,温州连续举办三场谢福芸回乡四卷本中国见闻录读书活动,并首次发布谢福芸拍摄的一段六分钟的影像资料。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会“动”的温州,原藏于英国电影档案馆,拍摄了白屋(今二轻局旧址)、城西教堂、艺文学堂(今墨池小学)、大街(今解放街)等场景及相关人物,弥足珍贵。来源:瓯风微信公众号
西安事变时的温州(节选)
谢福芸 文 程锦 译
我最近一次去上海是湿热的七月,女医生房东工作时汗珠缀满额头。我们都无比期盼秋高气爽的日子。十二月的上海却是雪虐风饕。冬天,其实整个长江流域不是雪就是泥,人们唉声叹气地向往着杏花初绽的春天。翟兰思夫人坐着朋友的车出门了。我挺不情愿和她分开,也坐着出租车出去。她早前决定租装修好的房子,空闲时就出门帮助生病或遭难的英国同胞。她的爱国情怀是实实在在的,不过工作量数月之内就翻了几番,而且正赶上最热的时候。很多在上海的英国家庭和公司都惨遭摧毁,重整旗鼓希望渺茫,恢复改善的可能性也很小。
我们依然为委员长及其夫人担忧。委员长夫人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英雄,不顾丈夫电报发出的命令,坐飞机到西安与他一道深入“虎穴”,我们都不敢指望他还活着。蒋夫人施展出女性全部的聪明才智,极尽克制又机敏行事,致力于救丈夫于水火之中。大家都悬着一颗心等待。
上海只是跳板,我们的目的地是上海以南三百英里的一座海滨城市:温州。我父母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二十五年时光。我在那儿度过了童年和部分少女时代。去温州,我渴望在温州度过圣诞节。父亲去世时,我说:“如今我要回温州去。”“我和你一起去。”表妹回应。放弃眼前的花花世界和各种娱乐,去中国一个微不足道的港口城市,这看起来的确可笑,不过表妹理解我。我去温州不是为埋葬死去的亲人,而是与他们重逢,寻求灵魂的平静,也许亲人所做的一切将激发我去效仿。
我们从中国蒸汽船航海公司办事处购买了汽船的船票,一两天后把行李和自己塞进出租车,登上了汽船的舷梯。出发的时刻总是这样阴冷黑暗。我们将在圣诞节当天一早抵达温州。汽船船长在过去一般是英国人、瑞典人或丹麦人,但自从一九二六年民族主义狂潮兴起后,根据中国法律,这些船必须要由中国人管理。上层甲板舱房门上依然用英语印着“First(大副)”、“Second(二副)”、“Engineer(工程师)”等字样。从最底层升上来的中国工程师微笑着告诉我们,轮船的英国发动机和他在白人工程师手下当学徒时一样运转良好。
沿着海边南下,天气很冷。岸边绵延的群山光秃秃的,一片萧索。没有无线电,我们只能自己跟自己较劲,万幸浑浊的大海还算平静。为了不让在旁服侍外国乘客的中国服务员失望,我们努力吃完午餐和晚餐提供的七道菜品,这是服务员自认的职责所在。
美妙的圣诞节早晨终于降临。醒来时外面晨曦初露,看啊,群山就在我的舷窗外飘过。船肯定已经转向进入河口,另一侧必然也是山。
“玛格丽特,”我走进隔壁船舱喊道,“我们到瓯江口了。”
“回去睡觉,”她说,一本正经的语气像个大妈,“才五点钟。不然今天天没黑你就该累坏了。”
她在船上提供的灰毯子里翻了个身,背对着我。我可不介意天太早,很快就穿好衣服上到甲板。自我幼时早早起床把手伸进圣诞长袜摸索礼物的日子以来,这是最美妙的一个圣诞清晨。记忆中亲切的群山在我身边缓缓流过,昏暗的平原躺在眼前。过去汽船一经过某个地方就会鸣笛示意,现如今一周开行三次,谁还在乎鸣不鸣笛呢?
“回到家乡忆起这些往事我真开心。”我迎着风对玛格丽特说。风刮得很大,像从约克郡高高的河堤刮过来,我们家族就起源于那儿的采石场。可爱的姑娘放弃了常识,来到甲板上,和我一起等着看温州开着枪眼的老城墙的第一眼轮廓。我们挽着胳膊握着手。她也深知,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不去缅怀珍贵丰富的过去而任其逝去。我们共同领悟到,来这里不是为了忘却,记忆促使我们活得更真实,接受现实,并无畏地探索崭新未来。我们告诉彼此,不要再执着于失去或亲人的离开,而是要深入他们留下的充实人生及其虔诚耕耘的精神宝藏。
天还很黑,来码头迎接的英国人举起防风灯向我们致意。他们出来得这么早,真令人感动——尤其当我们听说两批年轻基督徒唱圣歌唱疯了,分别在凌晨一点和三点两次唱歌叫醒他们!我们坐上人力车——过去都是坐轿子——通过毫无阻碍的城门入口,这里曾经是温州城东门设置工事的地方。也许中国最终卸下了防备,让新的生命灌注进来。我们经过又新奇又熟悉的街道。曾经狭窄的小巷,如今变成了宽宽的大街,街边是两层砖石商店,玻璃店面闪闪发光。仅仅十年,这儿就从乔治·默兰德的十八世纪英国荒野风景变成了令人愉悦的城郊风光。
医院的英国护士长在我们之前住过的老宅——“白屋”——欢迎我们。三十年前,在医院做护士帮忙的就只有我一位女性,如果十七岁的女孩可以被当作女性的话。如今眼前这位开朗能干的女性把自己全部奉献给了医院。医院扩大了很多倍,每年接诊量成千上万。十年前她是唯一的护士,如今在她手下培训的有四十位中国姑娘。
“最初的两个姑娘因为要护理男病人,跑回家痛哭不止,感到丢人,好几个星期不愿回来,”她笑着说,“不过现在她们乐意为病人做一切事。”
她叫了早餐。看,一位中国女仆进来了,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她。在女性裹足的过去,男性才能做仆人。她叫爱心,二十五岁,是个寡妇,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脚上再也没有束缚。
谈谈教堂吧。父亲在他管辖的教区里建起了差不多两百座大小不一的教堂,教区面积和威尔士差不多,也拥有美丽的群山、河流、山谷和平原。乡下每周都有差不多五百人聚在某个大市镇里,大约一百人聚在某个大村里,五十多人聚在小一些的地方。这些都是从我们立足的城西堂发展起来的。父亲在的时候,出席每月圣餐日聚会的能达到一千人。
城西堂是父亲建起的第一座建筑。他当时只有二十三岁,是很多事情都可以被原谅的年纪,尤其是在来中国之前他学的是法律,不是建筑。拳乱之后很多人改信基督,他不得不扩建教堂以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充满爱心的工人给高高的天花板加上雕刻,黑色立柱涂上清漆。由于健康原因,父亲去了北方,他的传教团,尤其是城西堂,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有一年夏天,台风把一堵基墙刮歪了一尺,这算是客观上的改变。欧洲大战爆发,来自母国的资金和人力支持锐减,可这些都不值一提,因为伟大的慈善壮举绝不是缺钱就运转不了的。从一九二七年起,民族主义浪潮来了,难民、士兵、持异见者轮流进驻教堂,在长椅间安营扎寨,破坏极大。有人甚至在刷了清漆的柱子上打钉扯绳晾衣服;有人在内墙附近烧火,把墙都熏黑了。
然而,台风对教堂结构造成的破坏根本无法同人祸相提并论。民族主义浪潮最激进时期,当时负责城西堂最年轻也最聪明的牧师在集会上宣称教会财产归会众所有,不再属于远在英国的任何慈善机构,他们拿走了很多长椅和物品以装饰另一幢对立的教堂和牧师楼。更糟糕的是:他分裂了会众,带走了一多半人员,其中包括很多知识分子和以世界的标准来看也比较富裕的人。留给传教团的有二三百人,都是忠心单纯的穷人。传教团选择了他们,给予他们教育和爱,建起医院,教他们的女人识字。最后,外国人无法在温州待下去的时候,这些穷人就留在教堂,耐心等待,直到外国牧师归来,确信自己不会永远被抛弃。如今回来的是二十六岁的英国人孙光德,出来传教一年了,正开始学中文,过去十二个月以一己之力维持着这座堡垒。会众开始回归。后来又有两位年轻的先生加盟,其中一位还在这里结婚。多么大的变化呀!
“最终,没有一个乡村分堂退出,”圣诞节清晨我们步行去教堂的路上,孙牧师说,“就只有那一个牧师离开了我们。我可以用生命信任其他十几位按立的牧师。他们自始至终在发挥作用,教堂才是他们的头等大事。他们有很棘手的问题要处理,有时候还要去最危险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尸位素餐。”
“您这么说真有趣,”我说,“但很重要。”
“我得提醒您,”他说,“我不能保证每个义务传道人都能这样。但不管在世界任何地方,两百个人里总会有人选择明哲保身。”
我们一边沿着拓宽的大街走一边谈话,转进了那些顽固不化的老巷子后,就不得不排成纵队前进。白铁匠敲着铁砧,家具店把家具摆在外头地砖上晒漆,清真肉铺挂出肉坨,冲着街上挑剔的顾客咂响舌头。两边是肮脏的污水沟,还没能像主街上的那样加盖。我们在一条巷口转弯,走上巨大简陋的台阶——过去这里曾拥挤无比——走进了父亲的教堂。
(全文刊于《瓯风》第十五集)